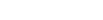聯系我們
南昌綠瑞康農產品配送有限公司
聯系人:肖總
電 話:13576919360
座 機:0791-88488287 88488626
微 信:13576272119
郵 箱:19406983@qq.com
地 址:青山湖區廣州路2099號針織服裝產業園一期2#-3廠房103
現在,如果在某聚會中隨口問句“關注的事情是什么”,大多數人會把“食品安全”排在前幾位。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,任何跟食品安全有關的說法 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,都能夠在短時間內廣為傳播。“解決食品安全問題”的呼聲持續不斷,有關部門也出臺了項又項“措施”。然而,相關事件還是持續不斷地出現。
消費者、主管部門和食品生產者,本應該是互相依存、互相制約、互相信任、互相促進的三角。然而,近幾年來,公眾的信任和信心或許已經創下了歷史新低,不知道是將進步惡化還是觸底反彈。
總而言之,在目前這種互相指責、互不信任的狀況下,問題的解決將越加艱難。
有的問題允許漫長的等待,然而吃飯的問題,不能。
自供運動,能走多遠?
2010年11月,據人民網報道:“出于對食品安全現狀的憂慮,部分省機關單位、大型國企、民營企業、上市公司、金融機構或個人自發組織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,形成自供或特別食品基地。”
這種方式,大概可以稱為“自供運動”。除了國家機關涉嫌濫用財政經費之外,商業機構和個人參與這種運動也無可厚非。任何特殊需求必然要付出特殊費用。對于商業機構和個人來說,“自供蔬菜”和昂貴品樣,是富有者的消費方式。從另個角度說,這還有助于在保持耕種的前提下提高農村土地的商業價值。此外,許多“自供蔬菜”并非由租賃者自己耕種,而是雇農民來種的,倒是能提高農民的收入。
對于參與這種運動的小部分人來說,這種方式能夠在定程度上解決問題。但是,從全社會的高度,這種方式對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,作用實在有限。理由有三點:
先,這種方式的高成本注定了只有小部分人消費得起。生產規模越大,成本越低,在食品生產上尤其如此。雖然這種“”結構避免了中間的流通環節,但是個小規模的菜地,要種植品種多樣的蔬菜,只能采取手工操作,人力成本可想而知。
其次,許多沒有種過地的人,會很天真而固執地認為只要不用化肥和農藥,問題就被解決了。他們并不知道“有機種植”遠遠不是那么簡單。旦蔬菜長蟲,不用農藥的結果往往就是沒有收成。多數土地不施肥很難長出蔬菜來。而使用“農家肥”的話,且不說如何獲得那么多農家肥,施肥的人力成本則更高。此外,未經處理的“農家肥”并不意味著安全。相對于化肥或者經過工業處理的有機肥,農家肥攜帶的病菌同樣會帶來不可忽視的健康隱患。
再者,對于城市中的般人,不大可能頻繁地去城外打理菜地。即使是自己種的菜,也只能采摘之后進行存儲。蔬菜的儲藏處理,又會帶來其他的安全隱患。如果只是租賃土地,雇農民種植,那么就跟定點采購類似。從報道來看,目前的“自供結構”主要還是依靠君子協議。旦發生糾紛,比如種出的蔬菜在數量和質量上達不成致,那么“放心菜”也就會吃得很“鬧心”了。
城市化、現代化注定社會必然高度分工。對食品安全擔憂,就“自供蔬菜”,那么對學校教育不滿呢?對醫療服務不滿呢?難不成都小規模地自己來?這其實就是過去的“企業辦社會”模式。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,國家機關和企業自己管理養老、住房這樣的問題效率很低。而食品問題甚至更加復雜繁瑣,換個角度來想:即使企業愿意花足夠的錢去為員工建立“基地”,可若是把那些錢分給員工的話會不會有更實惠的結果?
不考慮“自供運動”將會遇到的種種難題,光是成本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可行之路。而且,食品安全不僅僅是蔬菜的問題。實際上, 那些“自己種地”生產不了,或者“自供”成本更加高昂的食品,才是食品安全問題的重災區,比如加工食品、餐館食品以及肉類等。
以商治商,是否找到出路?
目前在這種小打小鬧的“自供運動”面臨著許多潛在的問題,時間長了必然會暴露出來。它如果發展成“企業辦社會”的模式,顯然沒有生命力。如果沿著現代化規模化,則可能發展成國外的IP模式或者FOP標簽系統。IP是“Identity Preserved”的簡稱,有人翻譯成“身份保持”。而FOP是“Front-of-Pack”的簡稱,指的是“以標志形式出現在包裝盒上”。
IP模式的核心在于對食品生產過程進行“全程追蹤”。從種子開始,經過種植、田間管理、收割、加工,直到消費者,整個過程都需要進行記錄。如果在整個過程中滿足特定的要求,比如什么樣的種子,使用什么樣的肥料等,就可以獲得IP認證。而FOP標簽,在目前的美國是在產品包裝上提供些營養評價方面的信息。面對中國消費者關注的安全問題,這個FOP模式也完全可以擴展成安全方面的評價。
從結果上看,IP模式和FOP標簽與“有機認證”、“綠色認證”有相似之處。不過,它們在運作上差異很大。“有機認證”和“綠色認證”是政府主導的,而IP模式和FOP標簽則不定。它們更多的是“信用保證”,可以由行業聯盟、專業協會甚至某個商業機構來進行。它們沒有“官方”做擔保,能否被消費者接受就完全取決于它們的信譽。在傳統心理上,我們更希望“官方保證”。但是,相對于“官方認證”潛在的濫用和腐敗,個需要自己建立信譽的認證體系并不見得更不可靠。
因為IP模式和FOP標簽可以涵蓋任何產品,以及產品的任何階段,所以它不會受到“自供運動”難以避免的產品種類的制約。而規模增大,也使得其成本相對于“自供運動”產品要低。不過,與普通產品相比,這些產品的生產和認證依然需要相當的成本來維持。換句話說,消費者依然要為“放心”而付出更高的價格。
IP模式和FOP標簽的勢在于對于政府監管的依賴減弱了。它對食品安全的保障,是通過消費者“用錢投票”來實現。從根本上說,就是生產者和認證者通過生產“放心食品”來賺更多的錢,而消費者通過付出更多的錢來購買“安心”。
食品安全,誰來管理?
不管是“自供運動”,還是發展到層次的IP模式或者FOP標簽,都需要通過消費者增加開銷來獲得“放心食品”。從社會成本來說,這是不必要的浪費。尤其是“自供模式”,本身就不是多數人能夠承擔的即使多數人能夠承擔,也沒有那么多的土地資源來實現。
作為社會問題出現的食品安全,很難依靠個人的“明哲保身”來保障。社會問題,終還是要靠社會來解決。每個人都切身相關,政府部門也再“下決心”。為什么經過那么多人的努力,形勢卻沒有好轉,公眾的不安甚至更加強烈呢?
食品安全事件的制造者都是食品生產者,所以他們承擔公眾的痛罵也是咎由自取。但痛罵畢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。任何行業,存在的根本目標都是為了賺錢。好企業與壞企業的區別,不是誰有道德,而是誰賺錢的方式合理合法。我們可以推崇和贊賞那些“高尚”的商人,問題是把食品安全寄托于企業的“高尚”,就像是把公正廉明寄托在包青天身上樣,完全不靠譜。
根本上說,生產者要賺的錢,掌握在消費者手中。賺錢的方式,就是提供消費者需要的產品。理論上說,消費者才是決定生產者如何生產的人。比如說,當消費者味追求“便宜”,那么生產者就會提供“便宜”的產品。但是保障食品安全需要相當的成本,價格便宜了就必然要在某個方面搗鬼。肉松就是個典型的例子。據報道,當年某個地區的肉松幾乎全部都采用了劣質原料。即使偶爾有試圖不隨大流的生產者,也會很快被市場淘汰。“劣幣驅逐良幣”,在中國的食品市場是如此突出。三聚氰胺席卷全行業,則是另個典型的例子。
不過,單靠消費者自己,也解決不了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問題。在多數情況下,消費者無力分辨產品是否合格,更不清楚低價的產品
是企業技術革新和“讓利”的結果,還是造假的結果。即使消費者愿意為“放心食品”付出額外費用,還是需要有人來告訴他們哪個產品是物有所值的。
所以,問題又回到原點: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,終還是要靠主管部門來推動。
主管部門,為什么只打雷沒下雨
中國挨罵多的政府部門,可能就是食品管理的“有關部門”了。每次有關食品安全的事件出現,“有關部門”定會被口水淹沒。
可能“有關部門”也很委屈 下的決心很多,干的工作也不少,為什么就沒有起到相應效果?
公眾和媒體喜歡說的話是“法制不健全”,經常是每出個事件,就呼吁“立法管管”。實際上,中國跟食品安全有關的法規并沒有大的問題,在很多具體規定上,甚至比美國、加拿大等還要保守和嚴格。過去的大多數食品安全事件,都可以在當時的法規框架內解決。只是,法規只能提供紙面上的保護當“有法不依,違法不究”的時候,“有法可依”的結果就是“嚇死膽小的,撐死膽大的”。
就具體的監管體系來說,中國目前這種多個部門“分段管理”的體制問題重重。是否禁用種食品添加劑,要由6個部委參與決策,“科學決策”就很容易被“部門利益”的扯皮邊緣化。在實際運作中,也就必然產生灰色地帶看起來有多個部門“可以”管理,同時也就意味著每個部門都可以等著別的部門去管理。經常有這樣的報道:為了某個事件,記者向A部門詢問,被打發到B部門;向B部門詢問,被打發到C部門繞了圈,可能又被打發回A部門。
即使“有關部門”想管,中國的市場現實同樣使得監管困難重重。美國的大型養雞場提供了99%的雞蛋,所以只要控制了他們,市場上就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安全事故。對于那些小型的養雞場,政府反倒管得不那么嚴。而中國的食品生產和流通是由大量小規模的從業者主導的。要對他們實施嚴格監督,執法成本可想而知。
更麻煩的還在于,這些部門都是某政府的下屬 也就意味著,他們要“配合”當地政府的“大局” 城市形象、財政收入、就業等。任何負面新聞出現,都可能被“大局”所“和諧”。所以,小生產者可能受到監管處罰,但是倒下了個,可能會站起來群。而個生產者如果做成了“大企業”,主管部門也就未必能夠對它進行監管。即使它們有違法行為,只要沒有出現人神共憤的結果,當地政府就不希望“影響企業運作”,甚至會進行“特別關照”。“誰找某某企業的麻煩,我就找誰的麻煩” 些地方政府腦把這樣的口號當作對轄區內大企業的支持。“有關部門”在想要查處這樣的企業之前,不得不三思是不是會被上司當作“找麻煩”。像三聚氰胺的使用,據說早已是公開的秘密,至少在出口寵物食品致死動物之后,主管部門不應該不知道它的非法使用。但是,在當地政府“揮淚斬馬謖”之前,當地的“有關部門”是工作疏忽沒有發現問題,還是迫于“大局”不敢管?
三方互動,才是答案
消費者、生產者和主管部門,構成了食品安全問題中的三角。問題的解決不是依靠哪個方面或者哪個部門單努力就能夠解決的。只有三方形成良好的活動互信,才能夠建立規范的市場。消費者付出合理的價格獲得放心的食品,生產者通過生產合格的產品贏得利潤,而管理者,則通過嚴格致的執法來實現“劣幣淘汰”、“良幣流通”。
當消費者愿意花更多的錢去開展“自供運動”的時候,其實已經做好了“用錢投票”的準備。而生產者,看到合法生產的商機了嗎?管理者,又做好了“只為食品安全負責,不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”的準備了嗎
生活中,我們經常聽到“某某食物中的某有害物質超標了多少多少”的說法。細心的人可能會發現:同種有害物質,在同種食物中,不同國家的“安全標準”不盡相同。這就產生了種“荒誕”的結果:有害物質在某個含量的種食物,在個國家是“安全”的,在另個國家卻是“有害”的。
“安全標準”的意義,是低于它就“安全”,超過它就“有害”么?要回答這個問題,先得知道“安全線”是如何劃定的。
問題:人體能夠承受多少?
任何有毒有害物質,都需要在定的量下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。要建立食物中的“安全標準”,先要知道人體能夠承受多少的量。理想情況下,是要找到這樣個量:當人體攝入的這種物質低于這個量時,就不會受到損害;而高于這個量,就有定的風險。該量被定義為“無可測不利影響水平”(NOAEL)。
在實際操作中,“無可測不利影響水平”的確定并不容易。先,“損害”如何界定?人體有各種生理指標,每項指標都有正常的波動范圍,如何來判斷發生了“損害”呢?其次,出于人類的倫理,我們不能明知種物質對人體有害,還拿人來做實驗,讓實驗者吃到受害的地步。
多數情況下,是用動物來做實驗。先,喂給動物定量的目標物質,跟蹤它在體內的代謝和排除情況。如果該物質很快被排出,那么問題就要簡單些。在定的時間內(比如幾個月)喂動物不同的量,檢測各項生理指標,以沒有出現任何生理指標異常的那個量為動物的“大安全攝入量”。如果這種物質在體內有積累,就比較麻煩,需要考慮在體內積累到什么量會產生危害,然后再計算每天每千克體重能夠承受的大量。考慮到動物和人的不同,需要把這個量轉化成每千克體重的量,再除以個安全系數(通常是幾十到百,有時甚至更高),來作為人的“安全攝入量”。比如說,用某種物質喂老鼠,幾個月之后,每天喂的量少于10毫克的那組老鼠都沒有問題,而喂20毫克的那組老鼠中有兩只出現了不良反應,那么10毫克就是這次試驗得到的“安全上限”。假如這些老鼠的平均體重是100克,那么每千克體重能夠承受的量就是100毫克。然后用這個數據來估算針對人的“安全上限”:如果采用100的安全系數,那么“安全標準”就定為每千克體重1毫克;如果采用50作為安全系數,“安全標準”就定位每千克體重2毫克。
有的物質對人體的危害有比較多的研究數據。比如鎘,在通過飲食進入人體的情況下先出現的傷害在腎臟。鎘會在腎臟累積,腎皮質中的鎘含量跟腎臟受損狀況直接相關。當腎皮質中的鎘含量在每千克200毫克時,大約有10%的人會出現“可觀測到的不利影響”。衛生組織把這個含量的四分之,即每千克50毫克,作為“安全上限”。然后考慮到飲食中鎘的平均吸收率,以及能夠排出的部分鎘,計算出每周每千克體重吸收的鎘在7微克以下時,對人體沒有可檢測到的損害。這個量叫作“暫定每周耐受量”(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,PTWI)。平均來說,這個量與每天每千克體重不超過1微克是樣的。對于個60千克的人,相當于平均每天不超過60微克。世衛組織采用這個“每周”的時間基準,是為了更好地表達“平均”的意思 比如說,如果現在吃了90微克,而明天控制到30微克,那么就跟兩天各吃了60微克是樣的。
還有些有毒物質對人體的危害缺乏直接實驗數據,對于動物的危害結果也是在大劑量下得到的。而通過飲食都是“小劑量長期攝入”,這種情況下會有什么樣的危害,就沒有實驗數據。科學家們會采用“大劑量”下得到的實驗數據,來“估算”在小劑量長期攝入的情況下對人體的影響,從而制定“安全標準”。這種“安全標準”就更加粗略,終得到的數字跟采用的模型和算法密切相關。比如燒烤會產生種叫做苯并芘的物質,在動物和體外細胞實驗中體現了致癌作用。這種物質在天然水中也廣泛存在,而在飲用水中的濃度范圍內它會產生什么樣的致癌風險,還缺乏數據。根據已知的數據進行模型估算,如果輩子飲用苯并芘濃度為每千克0.2微克的水,增加的癌癥風險在萬分之的量。所以,美國主管機構設定飲用水中的苯并芘“目標含量”是零,而“實際控制量”則是每千克0.2微克。
問題二:特定食物中允許存在多少?
知道了人體對于某種物質的“安全耐受量”,就可以指定它在某種食物中的“安全標準”了。
有的有害物質幾乎只來源于某種特定的食物,那么就用“每日大耐受量”除以正常人會在天之中吃的大量作為“安全標準”。比如有種叫做“萊克多巴胺”的瘦肉精,進行過人體試驗,在每天每千克體重67微克的劑量下沒有出現不良反應。美國采用50的安全系數,把每天每千克體重1.25微克作為普通人群的NOAEL值。假設個50千克的人每天要吃100克豬肉,得到豬肉中的允許殘留量為每千克625微克。
有的有害物質則存在于多種食物中。比如鎘,大米是大來源,按照每千克體重每天1微克的“安全限”,個60千克的人每天可以攝入60微克。假設大米中的鎘含量是每千克200微克(即中國國家標準的0.2毫克),那么每天不超過300克大米,就還在“安全限”之下。此外,水和其他食物也是可能的來源。世衛組織認為來自于飲水的鎘不應該超過“安全標準”的10%,假設個60千克的人每天攝入兩升水,因此把引用水中鎘的安全標準定為每升3微克。
問題三:如何理解“安全標準”?
顯而易見,所謂的“安全標準”是人為制定的。制定的依據是目前所獲得的實驗數據。當有新的實驗數據發現在更低的劑量下也會產生危害,那么這些“安全標準”就會相應修改。比如鎘,些初步實驗顯示在目前設定的安全量下,也有可能導致腎小管功能失調。如果在進步的實驗中,結果被確認,那么鎘的“安全限”就會相應調低。
此外,安全標準的設置中都會使用個“安全系數”。具體采用多大的系數,也是人為選擇的。不確定性越大,所選擇的安全系數也就越大。仍然以鎘為例,制定標準是基于生理指標,4的安全系數就可以了。而萊克多巴胺,制定基準是6名志愿者的宏觀表現,推廣到全體人群的不確定性就比較大。在制定萊克多巴胺安全標準的時候,美國采用的安全系數是50,而得到每千克豬肉50微克的標準。世衛組織和加拿大的安全系數就要高些,后得到的標準是每千克40微克。而聯合國糧農組織就更為保守,采用的標準是每千克10微克。中國則采用是“零容忍”,完全不允許存在。
安全標準的制定還與人群中對該種食物的普遍食用量有關。比如說無機砷,世衛組織制定的安全上限是每天每千克體重2微克,相當于60千克的人每天120微克。在歐美,人們吃的米飯不多,很難超過這個量,也就沒有對大米中的無機砷作出規定。而在中國,大米是主糧,就規定了每千克150微克的“安全上限”。或許基于類似的原因,日本大米中鎘的“安全限”就比中國的要高,是每千克400微克。
不難看出,這些“安全限”只是個“控制標準”,并不是“安全”與“有害”的分界線。比如說,如果個體重60千克的人,每天吃500克每千克含0.15毫克鎘的大米,是“超標”的;而如果只吃200克每千克含0.25毫克鎘的大米,則處在“安全范圍”。這就好比考試,總需要個“及格線” 考了60分的人通過,考了59分的人重修,但這并不意味著得60分的人和得59分的人就有根本的差別。
每天大量吃紅肉(指豬肉、牛肉和羊肉)會增加癌癥風險,平均每天吃140克的人比每天吃30克以下的人結腸癌風險高30%左右。對于有的人來說這個風險已經很大,所以愿意為了健康放棄吃這些肉。